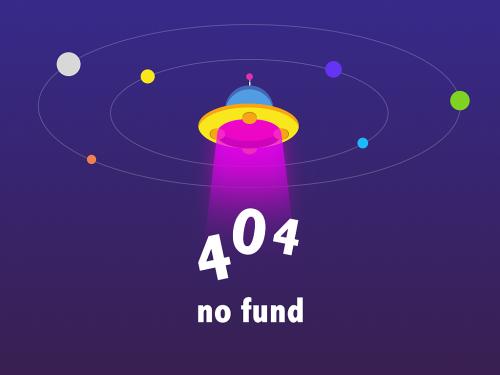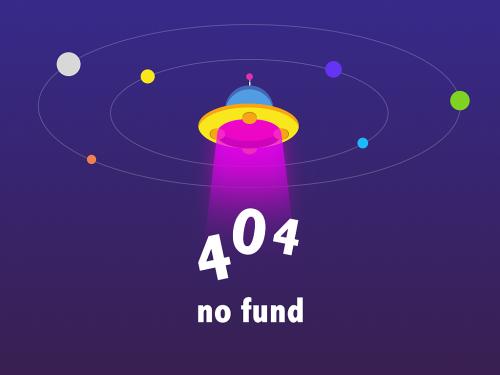|
克莱姆(klaus klemm)教授:
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政策首席顾问,曾任国际学生评估项目(pisa)顾问、德国“国家教育发展报告”顾问。 |
|
罗尔夫(hans-guenter rolff)教授:
德意志教育领导学院创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,曾任德国北威州州长咨询顾问、联邦政府海外学校管理中心教育质量管理委员会主席、德国教育科学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委员会理事长、德国社会学研究会教育社会学分会理事长、德意志科研基金会教育学评审委员会副主任。 |
主持人
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黄朔
访谈嘉宾
德意志教育领导学院创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尔夫教授
德国社会民主党教育政策首席顾问克莱姆教授
翻译
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俞可
罗尔夫教授和克莱姆教授40多年来对德国教育政策和教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bildung”,是我们在采访两位先生过程中无意中撞见的话题,它无疑会启发我们思考教育改革的更多含义。
“bildung”为教育改革带来新启发
记者:您怎样理解“教育”?
罗尔夫:关于教育的概念,德语中首推“bildung”这个词语,可以翻译成塑造、陶冶或是教育,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无法翻译成为其他语言。
这个概念在德国教育界使用得最为广泛,可以理解为“对于文化的个性化的接受”。世界上有多种文化,其中一种是你的母文化,教育一方面要促进和各种文化的互动,但同时要使你拥有自己的母文化。举个语言的例子,语言属于文化,文化是社会性的。教育充溢个性,每个人从社会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资源,对其进行个性化处理。这种个性化地对社会性资源的接收过程就是教育。同样,从德语语言环境中获取资源,因各自成长道路不同,每个人的教育结果各异。个体与个体的区别,不是文化的区别,只是因为个性化地接受社会性资源,才产生不同的结果。如果一个德国学生只懂德语,不懂其他语言,就会给他造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其他文化中提取资源的障碍,在其他人眼中,他就是“老土”。
克莱姆:对教育,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在历史当中反复会出现个人与国家的博弈,这里存在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。以纳粹为例,纳粹把社会、民族、国家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强加给个人,通过教育来渗透,通过教育来展现。现在的德国,却是个体利益甚嚣尘上。举个德国人和法国人的例子,他们都是很有教养的人,他们互相崇拜对方国家的文化,大家都不会想到,他们会拿起武器加入自己国家的军队。但是,由于教育的作用,出于经济与政治利益,他们最终会拿起武器指向对方,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对世仇。
罗尔夫:在德国,无论是在教育学界或是哲学界,教育的概念一直处于持久争议之中,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据我所知,只有俄罗斯存在类似争论。
记者:“bildung”这个概念更强调教育的哪些方面?
罗尔夫:德国也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,人文科学建立在哲学基础上,20世纪60年代之前占上风。而社会科学则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崛起,推动教育学转变为教育科学。
在德国,“erziehung”(education)和“bildung”两种教育概念是共生的。在知识社会,要强调人的素质。像国际学生评估项目(pisa),并非评估教育过程,而是评估学生的素养或胜任力(competence)。学生的素养或胜任力与社会需求挂钩,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服务,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完善。“bildung”却是指向自我完善。
“bildung”还有另一种定义,是指使个体全面发展,塑造各种素养协调发展的整体。为了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个人,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在全面发展的同时,实现个性化发展。现在的情况却是,从某种意义上说,技术主义导致了这样的后果:不是人在控制技术,而是技术在控制人。这样的发展,对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不是长远之计,我们一定要会回归“bildung”。有研究者作过一项调查,德国幼儿园的孩子不会倒着走路,因为他们被电视机这个保姆哺育,肢体机能由技术控制。
克莱姆:现在德国教育学界关于“bildung”的争论风平浪静,大家更愿意讨论教育能达到什么,与经济利益挂否,十分功利,而不是谈我们应该教些什么来达到一种自我完善。这种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教育,远离了“bildung”,远离了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理念。这种对于教育的认识是走不远的,我们还会回归“bildung”这个概念。
记者:在德国教育中,“bildung”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用?
罗尔夫:在德语中,“bildung”这个词由来已久,在18世纪开始与教育相勾连。当时的市民阶层想尽办法跻身上层社会。教育是除了血缘与金钱之外唯一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资本,由此形成西方的“社会开放”。这是一种社会进步。
不过,20世纪六七十年代,著名教育学家沃尔夫冈·克拉夫基认为,“bildung”有段“腐烂”的历史。一开始,市民阶层通过“bildung”挤进上层社会,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他们进入上层社会以后,又利用教育实施了“社会关闭”,不让工人阶层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,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德国的学校在四年级之后分成3类学校,工人阶层的孩子被分到最次等级的学校,他们难以跨入大学。当时有一种说法,教育是一种武器,具有攻击性与杀伤力,是市民阶层的自卫法宝。
记者:我们常说,德国“盛产”哲学家,“bildung”就体现出德意志民族的思想特点,也启示我们,教育要多从哲学那里汲取智慧。您认为,校长、行政官员是不是应该多读一点哲学书?
罗尔夫:现在的人很多是技术主义者,缺少反思,这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倾向有关。当今社会强调的是知识的经济价值,将人看作资本。不过,现在出现了一种抗衡的潮流,校长、行政官员发现他们需要价值、意义,这样才能从日常繁琐之中静心反思。有一段时间,《哲学入门》一直位列德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。书里,德国人能读到中国的老子。
教育改革需要恰当的时机吗
记者:教育与时代文化处于一种什么关系时,最适宜教育的发展?
克莱姆: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,也要考虑到文明进程。德国有很多外籍工人,在德国“经济奇迹”年代,他们从外国涌入德国,留在德国生儿育女,或是将生活在原籍的家庭带来,给德国社会造成了很大问题。通过何种手段使外籍人士及其子女融入德国社会,是德国面临的棘手问题。我们已经不能无视如此庞大的群体,外籍工人已经进入第二代、第三代了,只能通过教育。教育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利器。
记者:在什么时机下进行教育改革是适合的?
罗尔夫:我的博士论文就写到这个话题,教育规划是一个滚动的改革,改革是一种常态,所以原则上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期。回顾历史,我们更多时候使用的是“窗口期”这个词,也就是最佳时期。在联邦德国历史上,1968年掀起一场学生运动。对于教育改革,这场学生运动是很好的时机,可是德国错过了。接下来会有什么好时机,是不是错过了,难以预料。所以与其等待这么一场运动,还不如把改革视为一种常态。
克莱姆:现在更多的教育改革与人口挂钩。人口出生率锐减给教育规划带来很大挑战。《国家教育发展报告》中专门有一章谈人口发展和教育的关系。
判断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
记者:学校督导是对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评估的一种方式,您作为德国的教育督导专家,怎样看待学校督导对学校改革和发展的作用?
罗尔夫:在德国,学校督导每四到五年实施一次,每个学校必须接受督导。其中,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
在督导中,一般会有3位专家对学校进行大约3到4天的考察。除了考察知识性的课程,还要考察艺术类、文化类、体育类课程,观察课堂教学,观察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能否满足个体的需求。同时,学校还要提供文本资料,督导专家访谈相关人员。之后,督导专家要完成督导报告,其中包括关于教师、学生、教学等的分类报告,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。德国的教育督导人员是政府官员,由州议会任命。他们不执行教育部门的命令,而是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。对学校的督察、督导,各州会出台相关法律。学校经历过一次督导之后,也不觉得督导可怕。我曾作过调查,经过一次督导之后,学校就变得“乖巧”了,知道什么时候教育督导专家会来,做得不好的地方就要赶紧弥补、完善。
学校在需要政府支持,特别是资金支持的时候,才会认真对待教育督导报告。
当然,也有的学校接受督导之后恢复常态,但无论如何,督导会对学校有所影响。起初,有些教师和校长认为,教育督导只看浮光掠影。可是督导之后,专家提供一份反馈报告,建议到位,一针见血,让教师和校长心悦诚服。
记者:判断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?
克莱姆:可以有两条途径,制定学校发展目标和设置学业成就基准。例如留级生很多,我们就以减少留级生为目标,若干年后,我们发现留级生还这么多,没有达标,于是宣告改革失败。设置学业成就基准,就像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(pisa),假如德国学生在阅读素养方面排位很低,若干年后,跻身排行榜前列,可见改革富有成效。
在德国,一个衡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,就是社会分化度。社会分化有一系列衡量指标。教育是促进社会分化的重要途径。德国大学以及提供其生源的文理中学,过去被上层社会把持,现在由中产阶层掌控,但弱势群体仍遭遇排斥,社会分化度仍然有限。
德国《基本法》保障每个公民在出身、性别、种族、宗教上的平等。一个国家,不论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,都一定不能压制个体社会流动的自由以及全面发展的权利。
(本次采访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俞可翻译,谨致谢忱)
【链接】
教学文化与个体文化
克莱姆:教师文化分为教学文化和个体文化两部分,这两种文化对于学校教学发展有可能形成一种障碍。德国的教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,经历过见习,当教师之后,他们就关起门来自己讲课,他的教学不受校长和其他同事的影响。这种情况造成德国教师文化有教学文化和个体文化两种,给德国的教育发展造成了障碍。我们提倡的是教师专业化,教师要成为学习者,要学会与同事合作,要向自己的同事学习。中国教师当中不存在亚文化,有些教师与众不同,但是并没有形成亚文化。
学校大会对德国学校起重要作用
罗尔夫:在德国,校长和教师进行合作,制订目标,这个目标就是学生如何学好。德国联邦州里还有一种学校大会,对德国的学校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学校大会中,教师占1/2,学生和家长各占1/4,学校大会制订学校的目标、计划,甚至财政。他们对学校的目标、特色、项目等进行共同表决,但是不能决定某一个教师如何去做。
世界教育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
罗尔夫: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,文化呈现同化现象。由于不断地追求认知性的知识,追求认可度高的文凭,民族主义在教学文化中呈弱化状态。我的总体感觉是,文化中出现了同化趋势,同时,价值丧失严重,统治全球的是技术服务。世界教育出现了价值沦丧和教条主义两种极端。这就需要再一次回到“bildung”。(杨桂青 俞可 辑)
摘自《中国教育报》2016年5月12日第8版